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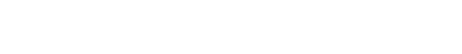
钍基核裂变能全国重点实验室 |
|||
|
-钍基核能物理中心-
|
|||
熔盐机械工程技术部 |
|||
仪控工程技术部 |
|||
熔盐化学工程技术部 |
|||
|
-核能综合利用研究中心-
|
|||
材料研究部 |
|||
钍铀循环化学部 |
|||
应用化学技术部 |
|||
氚科学与工程技术部 |
|||
核与辐射安全技术部 |
|||
应用加速器技术部 |
|||
反应堆运行技术部 |




(记者 许琦敏)为探寻宇宙婴儿期的奥秘,核物理学家成立了一个国际合作组RHIC-STAR:利用位于纽约长岛的美国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的相对论重离子对撞机(RHIC),让金原子核在接近光速下碰撞,通过螺旋管径迹探测器(STAR),来追寻各种基本粒子的蛛丝马迹,比如夸克、反物质。
这个合作组运行十余年,共发表了近两百篇学术论文,其中有一篇登上美国《科学》杂志,一篇登上英国《自然》杂志。这两篇论文都离不开一个人的名字——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马余刚。
属于中国STAR的荣耀
马余刚认为,这两篇论文是整个STAR中国组的荣耀。
两个金原子核在接近光速下对撞,会模拟出宇宙诞生时的那一声“啼哭”——产生大约等量的正物质和反物质。一对金核碰撞,大约会产生500个粒子,科学家通过筛选10亿次碰撞出的5000多亿个粒子,来寻找各种基本粒子的踪迹。
“大多数洋科学家都把目光集中在数量庞大的夸克、胶子上,但中国组则挑了块‘硬骨头’——寻找反物质。”马余刚介绍,在初次筛选中,反物质粒子太过稀少,很多国外科学家都放弃了这个“希望不大”的领域,可中国科学家准备迎难而上。
在国内,中科院上海原子核所(现中科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中国科技大学、清华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等6个单位结成联盟。2001年6月,STAR正式接纳了这些中国成员。2004年6月,STAR中国组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申请了约1000万元经费,开展该重大国际合作项目,马余刚担任负责人。
在实验中累积的5000多亿个粒子中,反超氚粒子(发表于《科学》杂志),只有70个;反氦4粒子(发表于《自然》杂志)更只有十几个。发现、证实这些粒子的存在,离不开高精度的STAR探测器及其子件“飞行时间探测器”(TOF),而后者正是中国组成员通力合作的成果。
“没有它,我们就发现不了迄今最重的反粒子。”马余刚说,STAR原有探测器在一定能量区域的分辨率不够高,找不出混迹在其他粒子中的反氦4,但TOF却能敏锐地抓住它的踪迹。STAR国际合作组发言人评述说:“TOF在该发现中起了关键作用,中国STAR组成员在数据分析中做出重大贡献。”
至今,中国STAR已走过了整整11年。他们正计划对STAR的高阶触发技术进行升级,以期找到更稀有的粒子。
兴奋却得保持冷静
马余刚说,面对一个即将诞生的重大发现,实在又紧张又兴奋。
对撞机一旦开动,数据就会源源不断地产生,学生必须“三班倒”地处理数据,马余刚会不断通过电话会议、email“盯进度”。他解释,数据在STAR内部是共享的,你不抓紧做,别人就可能先做出来。一旦听到风声,欧洲的同行也会开足马力来“抢第一”。
2011年4月,《自然》在线发表了马余刚负责的中国合作组作出重要贡献的新发现:新粒子反氦4。仅过了一个月,欧洲核子中心在一次国际会议上也报告了同样的发现——但他们已很难再就此正式发表论文。
不过,在看见新粒子的“可能性”后,一定要反复验证。他说,如同好钢需要百炼一样,宣布的新发现也得经得起同行、杂志编辑和匿名评审专家的拷问才行。
为了让整个团队保持紧张又审慎的状态,马余刚不仅每周召集学生开组会,还每月召集副研究员、助理研究员等职工开组会。“房子、孩子,他们身上的社会压力很重。”马余刚是个过来人,明白这个阶段最容易泄劲,得时时提点他们。
视野宽,基础牢
马余刚是浙江人,却为了喜爱核物理,跑去位于兰州的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读研。他的导师,我国著名物理学家、中科院院士沈文庆说,他很有钻劲,又很有思想。“只要碰上喜欢的题目,他会花比别人更多精力去钻研。”
1991年,他随导师来到当时的上海原子核所,把在兰州做的中低能重离子碰撞的核物理研究方向带到了上海。后来,参加了STAR的高能重离子碰撞领域研究后,他仍然坚守着原来的方向——这在核物理学界十分少见。
虽然在很多人看来,研究宇宙起源的高能核物理,与研究原子核状态的中低能核物理差别很大,但他却感觉两者息息相通。“高能核物理中,也会碰到中低能核物理中原子核状态改变的问题。”他举例,比如被牢牢禁锢在原子核中的夸克,在什么条件下才会融解出来,变成一锅“夸克汤”?
与核电站、核医疗设备等应用领域相比,马余刚的课题组属于基础研究,并不那么引人注目。可他组里的人专业基础扎实、视野宽广,所里一旦有新方向,需要输送人才,总会想到他这里。中科院启动了“钍基熔盐堆”的先导专项,就从他的课题组抽调了3名骨干。(转载自《文汇报》12月7日07版)
